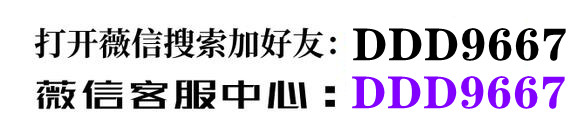唐纳德·特朗普第一次赢得了大多数民众的选票。他在对自己有利的巨大摇摆中当选美国总统,增加了他在首次选民、年轻选民、黑人选民和拉丁裔选民中的份额。他在收入低于10万美元的选民中获得了支持,而较富裕的选民更喜欢哈里斯——这将在2020年逆转阶级联盟。目前的计票结果显示,共和党的转变主要是由民主党选民的大量弃权造成的。这一结果与全球趋势相呼应。特朗普和他的新联盟现在将领导一个由印度、匈牙利、意大利、菲律宾、阿根廷、荷兰和以色列等极右翼政府组成的松散联盟。
极右翼的胜利节奏始于维克多Orbán在2010年匈牙利议会选举中的压倒性胜利。自从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2014年印度大选中获胜以来,这种情况几乎没有停止过: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英国脱欧公投以及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在菲律宾的成功都发生在2016年。两年后,雅伊尔·博尔索纳罗(Jair Bolsonaro)在巴西世界杯上破门。自疫情以来,意大利兄弟会赢得了2022年的意大利大选,哈维尔·米莱于2023年担任阿根廷总统。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本杰明·内塔尼亚胡的利库德集团与极右翼政党联合统治以色列。即使在极右翼不掌权的地方,极右翼势力也在壮大,比如在法国和德国。从长远来看,特朗普在2020年的失败和博尔索纳罗在2022年的失败是可以预测的总体上升模式的波动。
为什么极右翼总是获胜?是“经济,傻瓜”,正如詹姆斯·卡维尔在1992年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所说的那样?极右翼投票反映了经济上“掉队者”的抗议,这种观点相当流行。
这句话有一个真理的核心:经济状况是2024年特朗普选民的最大动机。自由主义者对“经济衰退”(公众对经济衰退的错误看法)嗤之以鼻,称GDP在增长,通货膨胀率在2.4%的温和水平。但总体数据并不能反映大多数人对经济的感受。价格比疫情前高出20%,更重要的是,食品等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28%。家庭债务是一个主要的压力因素。拜登还削减了疫情期间建立的一系列受欢迎的福利。不出所料,大多数人不相信标题数据。
然而,这种叙述仅仅触及了表面。首先,有证据表明,人们并不总是用钱包投票:从20世纪到现在的研究表明,简单的经济利益衡量标准并不能很好地预测投票行为。当然,经济很重要,但不是作为衡量总体福祉的简单指标。在这个空间里,人们根据自己对社会状况的看法来判断自己的个人地位。个人挫折通常只有在被视为更广泛危机的一部分时才会被政治化。其次,虽然极右翼在没有工人阶级支持的情况下无法获胜,但在美国、巴西、印度和菲律宾,它依赖于中产阶级支持的基石。此外,数百万人的经济生活在没有极右的情况下经常遭到破坏:大多数社会中最贫穷的人通常不太容易受到他们的信息的影响。第三,从严格的物质条件来看,当今极右翼的经济贡献微不足道,然而,现任政府对民族主义政府的宽容程度令人难以置信。
在印度,在平均消费者支出下降后,莫迪在2019年以6%的支持率再次当选。在菲律宾,随着“贫穷”菲律宾人的数量激增,杜特尔特的继任者小费迪南德·“Bongbong”马科斯在2022年赢得了58%的选票,增加了近20个百分点。即使在失败中,他们也表现得出奇地好。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平均收入的增长速度比他的前任慢,但他在2020年为自己的基础增加了1000万选民。如果人们用自己的钱包投票,为什么许多工薪阶层的美国人会支持一个承诺为富人减税的候选人呢?
经济困境的政治影响比“笨蛋,这是经济问题”所暗示的更为间接。经济冲击是由社会中现有的情感潮流所调节的。中产阶级和更富裕的工人可以认同富人,憎恨穷人、移民和威胁他们生活方式的“海绵体”。大多数情况下,怨恨的结果是无力的抱怨。受到冲击后,大多数人都无法面对自己的事业,并倾向于退出政治。
如今的极右翼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政治理论家威廉?康诺利(William Connolly)称之为“存在主义复仇的政治”。它用想象的灾难代替了真实的灾难。特朗普警告“共产主义”接管,并放大了“大替代”阴谋论。他的支持者怒斥“白人种族灭绝”和邪恶的猥亵儿童精英。他们不是反对不公正,而是诋毁那些威胁到阶级、种族和性别等社会等级的人。比起对抗系统,它们提供给你可以杀死的敌人。这是灾难民族主义。
它比选举影响更深远。自2010年以来,从网络法西斯主义的大锅中崛起的“独狼”谋杀有所增加。在德里和约旦河西岸爆发了大屠杀。在美国,义务警员袭击了“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者。英国和爱尔兰受到种族主义骚乱的影响。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拙劣的“叛乱”,例如2021年1月特朗普支持者对国会大厦的袭击,以及旨在阻止卢拉在巴西掌权的卡车司机封锁。
这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传染。新的极右翼非但没有因为集体暴力的爆发而名誉扫地,反而受到了它的激励。莫迪的上台始于他的家乡古吉拉特邦的反穆斯林大屠杀。特朗普2020年的竞选活动是由治安维持会暴力引发的。博索纳罗在经历了一个夏天的致命暴力事件后,从落后近20个百分点几乎获胜。
解决经济问题将化解其中的一些问题。大卫·布鲁克斯在《纽约时报》上承认,哈里斯的中间路线“不起作用”,民主党可能需要“接受伯尼·桑德斯式的颠覆”。
阅读更多
但颠覆不仅仅关乎“面包和黄油”。人们需要渴望的东西,需要让人兴奋的东西。这就是在桑德斯竞选和“黑人的命也重要”之后,在2020年推动民主党基础的原因,并反击了右翼的复仇政治。哈里斯的竞选团队隐晦地承认了这一点,他们含糊地谈到了“快乐”。但是,随着经济民粹主义被遗忘,极右翼的边界议程被接受,政府为内塔尼亚胡在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提供武器,这方面的空间已经很小了。
右翼的分裂不仅源于自身有毒的情绪波动,也源于自由主义的衰败和士气低落。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左翼需要自己的决裂。
理查德·西摩是《救助》杂志的作者和创始编辑。他的最新著作是《灾难民族主义:自由文明的衰落》
你对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有什么看法吗?如果你想提交回复不超过300字的电子邮件考虑在我们的信件部分发表,请点击这里。
为您推荐:
- 分享一款“乐趣麻将有挂吗(真的有挂)-知乎 2025-04-30
- 特朗普副总统表彰纽约“地铁治安维护者” 2025-04-30
- 通用工具“手机决胜麻将开挂免费软件下载安装”确实是有挂 2025-04-30
- 解析分享“手机麻将最新黑科技产品”确实是有挂 2025-04-30
- 罗伊·基恩指责利物浦球星,因为他对纽卡斯尔事件感到愤怒 2025-04-30
- 极右翼领导人正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指责“经济”或“落后者”并不能解决问题 2025-0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