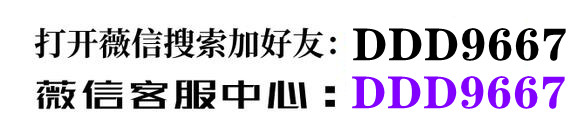上周末,柏林墙倒塌35周年纪念活动在英国没有举行太多纪念活动。这不是罂粟节。在文化共鸣方面,铁幕的揭开无法与纪念日相提并论。但它与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更相关。更令人痛心的是,如今美国人选出了一位与过去所谓的西方不友好的总统。
对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宫,没有哪个世界领导人会比这位坐在克里姆林宫的前克格勃(KGB)官员更高兴,他正渴望为苏联祖国在冷战中耻辱的失败复仇。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无法恢复昔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地位,但他可以让欧洲民主人士再次害怕莫斯科。他可以说服人们接受专制民族主义的恶性倾向,这种倾向扼杀自由规范,破坏任何地方的多边机构。这种恶毒的精神已经篡夺了正统保守主义,成为大西洋两岸右翼政治的推动力。用特朗普的话说,这比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当总统的想法更能吸引美国人。
美国民主不会突然消亡。让特朗普掌权的体制也可以像以前一样把他赶下台。对暴政的反抗是庄严载入法律、根植于美国文化的,但挑剔的政治破坏行为可能会破坏这些保护。特朗普入主椭圆形办公室时,将带着比他第一次上任时更有系统的颠覆宪法计划。他身边有科技寡头。他能在信息领域欺骗裁判。
新政府的执政信条将是意识形态信仰与腐败的混合体,由恩惠、个人崇拜和偏执维系在一起。这将是一个教条主义的盗贼统治国家,知道如何向正确的人宣扬正确的信仰的人将获得利润丰厚的工作和合同。这些政权将掠夺一个国家的虚伪正常化,同时声称要让它变得更强大。当服从领袖的意志等同于教义的正确性时,没有矛盾或羞耻。
对于受益于这种制度的人来说,选举失败不仅意味着收入的损失,而且意味着在新总统的领导下受到司法调查的威胁。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鄙视民主。他们不想进监狱。自由公正的投票机制必须被颠覆。
要在美国实现这一点,将比维克托?Orbán领导下的匈牙利,或雷杰普?塔伊普Erdo?an领导下的土耳其更难。这并不意味着不可能,尤其是在共和党控制参议院和最高法院,而反对派士气低落、意见分歧的情况下。
如果成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将被人们记住,就像35年前在柏林升起的太阳落下一样。在冷战中获胜的理念将不再在华盛顿盛行。特朗普的右翼有时仍将自己等同于所谓的“西方”,但在他们口中,这是一场保护白人基督教世界免受大规模移民影响的十字军东征,而不是自由多元主义或法治。
后西部时代美国的残酷现实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对英国来说,这是一场严重的危机。英国视美国为最重要的防务和安全伙伴,同时又依赖与欧洲的贸易实现繁荣。
曾几何时,这是一种具有巨大利益的地缘政治平衡。英国是华盛顿在布鲁塞尔最好的朋友,也是欧洲与白宫联系的热线。放弃这一地位让2016年的英国退欧成为一个糟糕的主意。它没有很好地陈化。
这让英国在特朗普准备发动的贸易战中严重暴露。他还会让欧洲变得更不安全。这些变数包括他对北约的关心程度有多低,他会在多大程度上安抚普京,他对欧盟领导人的敌意有多大,以及他的政治在欧洲大陆选举中的感染力有多大。
这让凯尔·斯塔默陷入了令人反感的境地。强大的现实政治潮流要求与任何一届美国政府保持亲密关系,无论现任总统可能多么令人反感。在国家安全利益紧密交织的情况下,正义的脱钩不是一个严肃的选择。但作为保持这种甜蜜关系的代价,特朗普将要求附庸,这将使斯塔默建立更紧密欧洲关系的雄心复杂化。
英国可以继续寻求与欧盟达成一项新的安全协议,同时卑躬屈膝地寻求美国关税的特别豁免。也许斯塔莫的手够稳,能穿那根针。但仅仅是暗示与特朗普结盟,就会让任何有关放宽英国进入单一市场的讨论变得糟糕。
英国将面临来自各方的压力,要求其尽快增加国防开支。但瑞秋?里夫斯(Rachel Reeves)预算所依据的增长模式,已经被日益抬头的保护主义前景打乱了。这是在特朗普试图消除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引发混乱之前。
现在还为时尚早。唐宁街10号不愿就事件发表连续评论是可以理解的。到目前为止,这些都是传统的外交陈词滥调。不可思议是斯塔默的默认风格。他不卖艺,尤其是当赌注很高的时候。
但是假装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是要付出代价的。没人买。工党的外交政策在11月5日爆发。A计划是老式大西洋中部桥梁角色的一个版本,一开始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它依赖于假装英国脱欧是过去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已经翻过了一页。事实上,这是对国家战略地位的一种恼人的、自我加重的伤害。不承认这一现实,就不可能对摆在面前的选择做出有意义或诚实的描述。
工党有令人信服的选举动机,不会以反对党的身份去那里。斯塔默周围有很多人仍然从这个角度看待英国退欧,认为应该停止这场对话,以免惹恼摇摆不定的选民;这是一个不可收拾的家庭疮疤。
但特朗普的胜利再次感染了伤口。这让英国在后西方世界显得孤家寡人。缺乏好的选择并不是假装没有紧急情况的理由。围绕英国百年来最大的战略失误而局促不安、吹毛求疵并不是一条可持续的道路。
斯塔默当时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然而,英国在欧洲问题上的政治辩论是如此的变态,以至于唯一允许的条款是由那些被证明完全错误的人决定的。一直以来都是正确的被认为是一种弱点,禁止告诉别人它是怎样的。
现在,这位首相再一次面对着必须书写英国在世界上角色的空白页。不敢指出问题所在的政策未能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也许是时候重新开始了,这次从真相开始。
拉斐尔·贝尔是《卫报》专栏作家
为您推荐:
- 分析必看“微信里的微乐三打一有挂吗(详细真的有挂)-知乎 2025-04-27
- 范加尔向曼联的标志性人物致敬,展现了他的本色 2025-04-27
- 玩家必看教程“手机微乐斗地主怎么保证牌好”确实是有挂 2025-04-27
- 青少年准备逃离乌克兰-时报 2025-04-27
- 给大家通报一下“微乐跑得快可以开挂吗”其实确实有挂 2025-04-27
- 韩国将利率下调25个基点 2025-0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