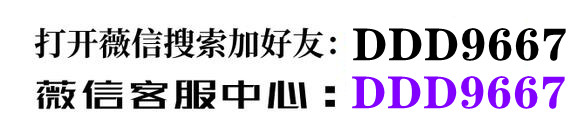这个故事是10月6日星期日生活版的一部分。看全部13个故事。
直到29年后,我作为一个新生儿接受了听力测试,结果显示我的听力既不是100%,也没有坏到值得担心的程度,我才真正调查了我可能有严重听力损失的可能性。
大约10年前,朋友们开始经常提到,为了让我跟上社交场合的节奏,他们经常不得不重复自己说过的话。两年半前,我意识到自己花了很多时间读唇语。这并不是说我完全否认;它更像是隔离和无知的幸福的混合体——直到一场全球大流行让地球上的每一张脸都戴上了外科口罩,让我无法将视觉信号转化为它们低沉的声音所代表的意义。
甚至在COVID-19之前,Cait(队友Caitlin ford)有时会开玩笑地捂着嘴,因为她看到我在看着她的嘴唇动。而不是接受她的观点,我会笑着告诉她不要像个白痴一样,然后再次提出这个问题。
当我最终在2022年10月寻求并得到诊断时,这在遗传学上是有意义的。我哥哥的听力损失比我严重得多,他在两岁零九个月时被诊断出来,因为他的语言听不清。他戴上了助听器,并接受了高强度的语言治疗。在学校里,他的老师在衣领上系了一个小麦克风,直接对着他的助听器广播,帮助他在嘈杂的教室里学习。
由于萨姆的损伤,我的耳朵每六个月检查一次,直到我两岁,然后每年检查一次,直到我六岁。测试结果总体上还不错,但事后回想起来,我确实想知道,我是否比大多数人都更努力地学习,才导致我在上课时容易失去兴趣;如果,也许,我不能完全跟上老师,所以开始我自己的,不太学术的对话,而不是与同龄人。我可能只是有点淘气,但我不记得自己是那种为了吵闹而让人讨厌的孩子。
多年来,女孩们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但我就是不太在意。即使在COVID期间,当口罩阻止我理解这么多时,我也顺其自然。对我来说,转折点可能是我和Kirst(合伙人Kirsty Smith)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她说话很温柔。有时我几乎听不见她说话,她不得不一直重复她的话。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喝咖啡,科斯蒂通过扬声器点了咖啡。当收银员通过她的扬声器回答时,听起来就像一堆乱七八糟的单词。我完全搞不懂。但科斯蒂完全理解。那可能是我的时刻。
一天早上,我在去训练的路上给山姆打电话,大声说:“我想我需要检查一下听力。”尽管萨姆已经完全习惯了在我们家佩戴助听器,但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在电话里跟他说了我的症状。
这很有帮助,因为他确切地知道要寻找什么,并在这个过程中消除了一个额外的障碍。我预约了,想去检查一下耳朵,然后就走了。情况下关闭。我告诉听力学家我们的家族史,我经常唇读,在有很多背景噪音的嘈杂环境中挣扎。我还告诉她,当有人在电视开着的同时和我说话时,我会感到不知所措。
然后我坐在这个小隔间里,戴着耳机,每当我听到不同频率的声音时,我就必须按下一个按钮。演出结束后,我走了出去,和她一起坐在电脑屏幕前。它展示了一个图表,其中两条线看起来很正常,而第三条线则远远低于其他线。她告诉我我有高频听力损失,或者类似的话。我几乎不记得了,因为我一直在等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肯定需要助听器。我还了解到,如果你不戴助听器,耳朵里的肌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恶化,因为它们没有得到足够的刺激。
我想她意识到这很难接受,因为她停下来问我感觉如何。她一说完,我就哭了起来。我内心深处知道,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只是很多现实的冲击同时袭来。终于确定了,这也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们又谈了一些各种助听器的选择,然后我就回家了。
在路上,我用facetime和lan(队友Alanna Kennedy)和Cait聊天,我哭得很伤心,甚至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打电话给他们。我一直想把它弄出来,但他们越来越担心我要告诉他们什么可怕的事情。当我终于脱口说出我需要助听器时,其中一个笑了起来,说:“感谢上帝。我们以为可能有人死了。”他们都说他们为我感到骄傲。我回到科斯特家,又哭了一场,然后打电话给家里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在那之后,我很快就进步了。大约10天后,在我去参加对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国际友谊赛之前,科斯蒂和我一起去安装了助听器,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们去取了他们。就在我第一次戴上助听器之前,科斯蒂问我能不能听到外面的雨声。我不能。他们一进来,我就能。事后回想起来,我听不到这样的事情真是太疯狂了,但我显然没有多想。
第二天,我们一起散步,我听到了叮当声,但不知道是什么。最后,我问了科斯特,她说那只是钥匙在她口袋里动来动去。几天后,我们出去吃饭,我用餐厅的背景噪音来调整助听器附带的应用程序上的设置。你可以调节音量,把注意力集中在你眼前的东西上,也可以吸收远处的噪音。
最大的新事物是音乐——我能听清楚歌词了!整件事都不真实。我的助听器也有蓝牙,所以我的Spotify可以通过它们播放,电话也可以通过它们接通。我最终选择了和我哥哥一样的款式,我们花了一点时间比较。
科斯蒂拍下了我捡起它们的过程。当时,她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它送给我的家人——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会很高兴。我们最后把它编辑了一下,我把它发到了Instagram上。这是一个很酷的视频,但我也认为,通过主动将我的新闻发布到世界上,我可能不必处理每次有人注意到他们时的关注。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马上看到,就能完成了。“我最亲近的人都知道我躲避这一天有多长时间了,但在这里,我可以瞥见改变我一生的一天,”我写道。“昨天我拿起了我的助听器,虽然这是我需要习惯的东西,但我对这一点小小的调整非常感激。”
我没有预料到人们的反应。我收到了许多父母、孩子和其他成年人的信息,他们也回避了听力损失的现实。直到今天,我仍然能从公众那里得到反馈。
2023年圣诞节刚过,我和家人在伦诺克斯黑德(Lennox Head),一位母亲在一家随意挑选的购物中心走近我,感谢我为她的孩子们树立了榜样。她自己也植入了人工耳蜗。2024年2月,几个戴着助听器的女孩来到我们对阵阿森纳的比赛现场,只为见我并感谢我。我想在体育界没有人有听力损失的榜样。我有萨姆,但大多数人都是自己经历的。现在我和Audika合作了。他们在澳大利亚重新测试了我的听力,给我配了另一副。
我已经决定在训练和比赛中不戴助听器,特别是考虑到我的首发位置感觉很不稳定。我不希望任何大的改变会分散我的注意力,导致错误。从那以后,我穿着现在穿的这双鞋训练了几次,但我不知道我是否会在比赛中穿着它。听力损失对我演奏的影响不大。我一直在说话,而不是相反,即使我戴着眼镜,我也不可能在5万人的观众席上听到别人说话。
《麦肯齐·阿诺德》节选(企鹅兰登书屋),10月8日发售。
让最好的《星期日生活》杂志每周日早上送到你的收件箱。在这里注册获取我们的免费时事通讯。
为您推荐:
- 莫迪总理在为金砖国家领导人举行的晚宴上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热烈欢迎(观看视频) 2025-04-19
- 教程指点“玉兔追月软件作弊”真实有挂 2025-04-19
- 重磅揭秘“三木互娱有没有免费挂”真实有挂 2025-04-18
- 教程分享“手机微信麻将怎么开免费的挂”分享用挂教程 2025-04-18
- 英国呼吁为中东人道主义援助筹集资金 2025-04-18
- 重磅揭秘“德扑之星开挂方法”确实是有挂 2025-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