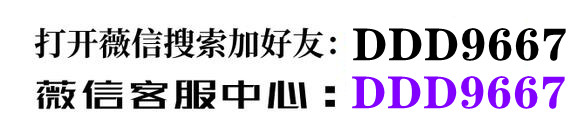对于许多读者来说,我的缺席可能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那些少数发现我失踪的人可能会胡思乱想:也许施莱弗在反对不受控制的非法移民方面越界了,所以她最终被解雇了。这种解释更为平常。
六年前,我被诊断出患有听起来很笨重的椎体滑脱:我下脊柱的一根椎骨偏离了直线,挤压了我右臀部和腿部的神经。我一直在处理,但情况恶化了。到今年夏天,我几乎不能完成15分钟的步行,而且——极限——我不能打网球了。8月7日,在纽约的国际医疗中心,我接受了一次大的背部手术(L4/L5融合,器械和减压,如果我们要花哨的话)。
我一直很害怕这次手术。我咨询过的每个人都建议说:“无论你做什么,都不要再做手术了!”他们都推荐宠物替代疗法,通常是傻乎乎的替代疗法,没有一种能让我那块偏离方向的骨头回到原来的位置。我在健身方面很虚荣,我不愿意把几周的恢复时间浪费在愚蠢的散步上,而我忽略的俯卧撑和仰卧起坐却退化了。在六十多岁的时候保持肌肉是完全可行的;在六十多岁的时候锻炼肌肉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回想起来,我对手术并没有足够的恐惧。
当我从麻醉中苏醒过来时,手术小组报告说一切都很顺利,但在深入了解了细节之后,他们对我日常承受的痛苦感到惊讶。我自以为很坚强,把这句话当作一种恭维。然而,当我回到布鲁克林的家中,麻醉药渐渐消失后,我对自己高得惊人的痛觉阈的任何夸耀都持续不了五分钟。最初的警告是,背部手术后的恢复期非常痛苦,这一警告一直是抽象的,而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应该知道,疼痛绝不是抽象的。
我仍然不确定我的药物治疗是否管理不善,或者是否几乎无休止和加速的痛苦是任何背部手术患者的形式,而不是“坚强”,我是一个绝望的懦夫。但我的痛苦却越来越强烈。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对羟考酮上瘾,它没有表现出任何欣快的品质。更糟糕的是,药物起效的时间越来越长,起效的时间也越来越短,所以每次给药之间,我都会痛苦地熬过整整90分钟,疼痛没有缓解。我睡不着觉,我翻腾着被褥,抓着床单,徒劳地呜咽着,把我可怜的丈夫赶到楼下的沙发上。
第九天,当我从床上爬起来的时候,我的手和脚都感到刺痛和麻木。我情绪不稳定,又一次需要一个助行器来蹒跚地走过客厅,我感到头晕。在持续的疼痛和眩晕无力之间,我在三个晚上中有两个晚上进了急诊室。此后,我接受手术的那家医院再次接纳了我。
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我失去了走路的能力。如果我想站起来,我就倒下了。这使我不得不使用床边的便盆。同时我做了核磁共振和血液检查,但结果都不确定。没人知道我怎么了。
最后,我的手术团队决定,如果他们找不到我有什么问题,我就没有问题。这些医生突然在我面前冷静下来,保持着情感上的距离,好像我得了什么病似的。我被告知我有精神疾病。我身体上的缺陷都是我的幻觉。这里不是精神病院,所以他们让我出院了。后来,我丈夫在我的笔记中发现,团队也怀疑我有滥用药物的问题。这些结论毫无根据。我没有毒瘾史,也没有精神不稳定。但他们希望与我一刀两断。
我被送到布鲁克林一家破旧的康复中心。由于我无法承受自己的体重,那里的护士把我裹在尿布里,因为他们不想腾出工作人员陪我去厕所。随后,我的手术团队痛斥说,施莱弗来了之后就“大小便失禁”了。想象自己像金枪鱼三明治一样被包在玻璃纸里;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别无选择,只能“失禁”,以免你爆炸。为了不让我受这种羞辱,我从爱荷华州飞来的哥哥和我丈夫轮流睡在我房间的椅子上12个小时,这样他们就可以抱我去厕所了。我再也不能吃东西了,我在蒸发。我丈夫以为我要死了。他也许没有错。
幸运的是,我被安排做最后一次神经测试。主治医生并不认为我疯了。她的诊断结果和我在谷歌上搜索的丈夫、哥哥和一个朋友几周前得出的一样:格林-巴勒综合征,是手术引发的。她赶紧把我送到另一家医院,在那里他们立即开始给我注射免疫球蛋白。我又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星期。
你可能会认识到,GBS是某些新冠疫苗不太为人所知的副作用。GBS也是一种常见的副作用,以至于猪流感疫苗被撤出了市场。那是因为没人想要格林-巴罗综合征,现在我知道原因了。
我预计会康复,不过恢复正常可能需要两年时间。由于自身免疫性疾病,身体会攻击自己的神经系统,我像个新生儿一样虚弱。我连一罐雪碧都开不了。唉,这种卑微的坏运气并没有改善我的性格。
我唯一的收获是感谢我的兄弟和丈夫的慷慨厚意。我不希望我的bête女友(甚至是卡玛拉·哈里斯!)但我希望任何遭受这种悲剧的人都能有家人以最切实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爱:把你绑到厕所,把你的短裤拖到膝盖上,把它们拉回你萎缩的屁股上,然后拥抱你回到床上。这才是真爱。
订阅每月只需1英镑
n
每周注册两篇文章
已经是订阅者了?登录
为您推荐:
- 分享技巧”福建兄弟十三水APP开挂教程”真实有挂 2025-04-18
- 教程指点“微乐三代二外卦神器下载安装”真实有挂 2025-04-18
- 苏丹霍乱病例上升至30880例,登革热病例上升至6011例:卫生部 2025-04-18
- 教程分享“微乐甘肃麻将小程序怎么开挂(真的有挂)-知乎 2025-04-18
- 我们对这个季节新西兰飓风风险的了解 2025-04-18
- 必看技巧“和棋生财有挂吗”(原来确实是有挂) 2025-0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