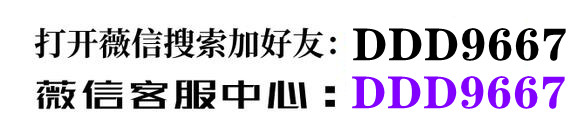我68岁的祖母和我语言不通。她说阿拉伯语,虽然我能听懂她的话,但我还是用英语回答。我喜欢把这件事(以及其他一切)归咎于我的父母。我们在墨尔本郊区长大,远离他们在黎巴嫩度过童年的地方,他们没有想过要教我。或者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而是专注于自己的小生意。
去年我祖母来澳大利亚参加我哥哥的婚礼时,我妈妈担任翻译。大多数早晨,泰塔会煮黎巴嫩咖啡,抽细烟,而我和父母则坐在前院,听她讲故事。她做了warak enab(用肉和米饭填满的藤叶),边做边教我最好的卷饼方法。她唱歌时,声音充满了整个屋子。在婚礼上,她用阿拉伯语向这对新婚夫妇致辞。她那微妙的语言和她的热情使房间里的每个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
我很幸运能拥有这样的时刻。但直到最近,我才完全欣赏他们。泰塔上次来的时候,我还在长大。我的时间都花在听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的歌和未成年人喝酒上——基本上是为了被视为“正常”而做的一切。也许正是因为她要回到一个处于战争边缘的国家,才使这次访问变得更加特别,也让我更加珍惜我的家乡。
四个月后,她一起度过了圣诞节、新年和一个完整的澳大利亚夏天,是时候回家了。
每次我妈妈和她说再见,她都会哭,好像她又回到了十几岁。但这一次,说再见的感觉不一样。我发现自己在想,如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她呢?我想知道我妈妈是否也在想同样的事情。
尽管紧张局势升级,但我能感觉到泰塔很感激能回到她生活了一辈子的黎巴嫩沿海城市杰涅赫。这是她的社区,她的孙子,她的儿子,她的妹妹,公寓,她的日常生活。即使她不想回来,她也不像我有双重国籍。她不能因为澳大利亚更安全就呆在那里。
我觉得我的祖先最可悲的是,他们习惯于感到不安全;战争的常态。当妈妈谈到她小时候的战争记忆时,她回忆起和邻居们一起玩耍,同时躲避炸弹的情景。但现在,她知道情况更糟了。“在我们那个年代,你可以躲在庇护所里,”她最近在晚餐时说,仿佛她在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但是这些新的炸弹,它们深入地下,所以无处可去。”
在我们告别后的六个月里,随着中东的冲突升级,从加沙蔓延到黎巴嫩,我养成了一种焦虑的习惯,每天都要查看我的泰塔的WhatsApp状态。我很少打电话或发信息,主要是因为我不想让她担心,但这是我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也是我睡觉前做的最后一件事。“现在活跃起来”让人放心。“10小时前在线”让我充满恐惧。
她一周前发来的最新语音备忘录伤透了我的心。
“愿上帝保佑你,因为我担心你的作品被曝光。别为我担心,我很好。我们能听到爆炸声,但还没到我们住的地方。我很爱你们,你们要保重。别太为我们担心,我的心(一种爱称,意思是“我的心”)。”
我不知道她的情况到底有多糟糕,因为她会忽略自己的需求,或者忽略细节来照顾她的家人。有可能她并不完全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因为政府并没有让他们了解情况。他们只是听到炸弹声,然后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形势不容乐观。我很难阅读任何新闻或专注于工作。我几乎不喜欢和朋友出去玩。我害怕把这些感受写出来,以防人们因为我的政治倾向而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或者说我离这种情况还不够近,无法感受到这种悲伤。
我想知道其他24.8万黎巴嫩裔澳大利亚人和中东侨民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每天都害怕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或者你的家人是否安全。如果终有一天,我们能再次回到我们的故乡,它看起来还是一样的。
悲伤会以奇怪的方式表现出来。我对父母移居澳大利亚给我带来的安全感到内疚。为什么我能安全,而我奶奶却不能?我为从未学过阿拉伯语,也不能每天和奶奶交谈而感到内疚。我为凌晨一点还在家庭聚会上谈论身份政治而感到内疚,而她却生活在另一场冲突中。我很内疚没能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
Abbir Dib是一名记者和观点作家我住在墨尔本。
为您推荐:
- 杰米·奥利弗的“绝对美味”健康早餐食谱使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食材 2025-04-18
- 必看技巧“多乐跑得快小程序怎么拿好牌”其实有挂 2025-04-18
- 必看技巧“关帝联盟开挂教程”(原来确实是有挂) 2025-04-18
- 教程分享“微乐云南麻将有挂吗”确实是有挂 2025-04-18
- 威克,其他人回避了里弗斯对LG杀人、纵火的调查 2025-04-18
- 据报道,波音公司打算通过出售与美国宇航局的业务退出太空竞赛 2025-04-18